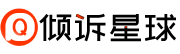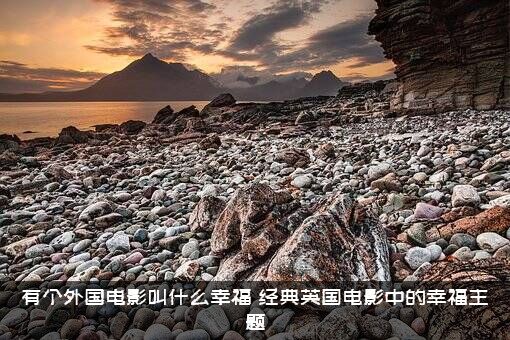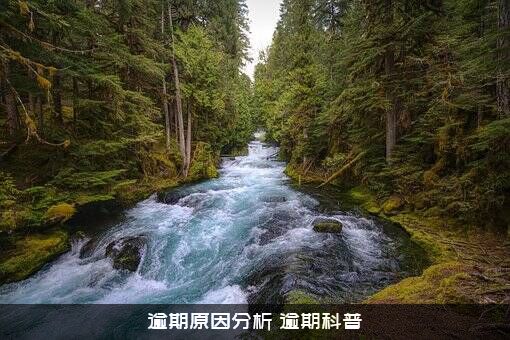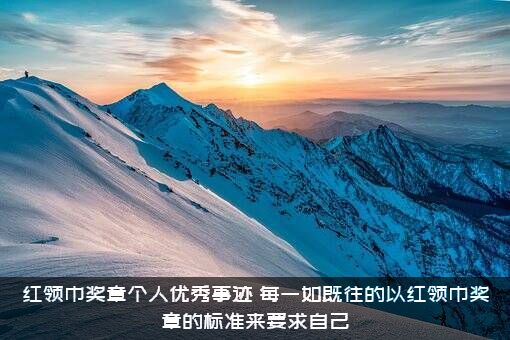多谈谈问题丨今天为何如此
无意义和虚无是从哪来的?其实就是从信仰大退潮开始。信仰死去之后,人们找不到社会和生存的意义,所有的行为都是在解构,都是在批判,但是并没有重建。”景凯旋与张乔木的观点几乎一致,他借帕...,接下来具体说说一个是今天为何如此
《多谈谈问题》应该是今年读过较好的一本国内思想界访谈录,整体读完,全书其实一直围绕着两个问题在反复探问:一个是今天为何如此?另一个是:我们又将如何?
靠前个问题:今天为何如此?
对张乔木(思想史万有引力讲述者)来说,今天人类的境遇,是现代性导致的信仰缺失,人类逐步丧失意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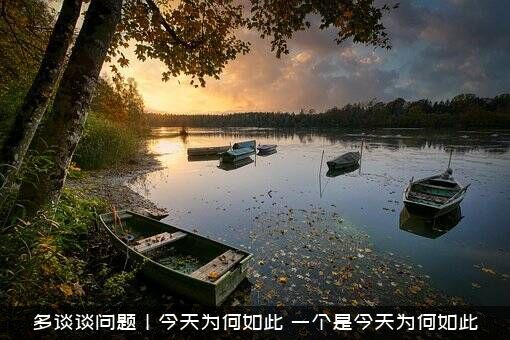 “现代性的开始,就是信仰的崩溃,人们在世俗化世界里看不到任何希望和成就。20世纪初现代主义开始萌发,就是要对抗虚无,对抗无意义。无意义和虚无是从哪来的?其实就是从信仰大退潮开始。信仰死去之后,人们找不到社会和生存的意义,所有的行为都是在解构,都是在批判,但是并没有重建。”
“现代性的开始,就是信仰的崩溃,人们在世俗化世界里看不到任何希望和成就。20世纪初现代主义开始萌发,就是要对抗虚无,对抗无意义。无意义和虚无是从哪来的?其实就是从信仰大退潮开始。信仰死去之后,人们找不到社会和生存的意义,所有的行为都是在解构,都是在批判,但是并没有重建。”
景凯旋与张乔木的观点几乎一致,他借帕托什卡的一句话来解构这个现实: “现代最大的危机就是意义的危机。” 正是这种危机导致了人类的孤独和原子化。
信仰消失,生存意义消解后,现代人没有了任何敬畏,世俗人文主义者彻底摆脱了绝对者之后,却发现自己孤独地面对世界,无所依傍,正如布拉加所言:“ 个体只能将自己的影子当作依靠的支柱。”
进入原子化生存的人类,只能孤身面对无限的虚无,而互联网的出现又加速扩张了这种虚无……
戴锦华借德尔·托罗“认识论危机”的论断,来对如今的互联网结构进行了解析:“大数据、精准投放、推送――所形成的 “信息茧房”,令我们无法从互联网上获取新知、发现未知,甚至丧失了求知的意识和愿望。经由网络、经由传播,我们只会印证自己的已知,确信自己的正确,因此我们无从形成新观点,丧失了质疑既有观点和立场的可能性。”
正是这种“独断的偏执”,促成了当下大规模的“网暴”情绪, 为什么人们越来越愤怒了呢?尤其是在网络上可以恣肆到如此程度?
戴锦华的回答是:“这一切,都与冷战终结后两大世界性趋势有关―― 一则是急剧的、加速度的贫富分化、阶级固化;一则是整个世界丧失了全球资本主义之外的另类选择与乌托邦冲动的全面耗竭――相伴生,累积着越来越强烈的戾气。极度消极无助的社会情绪。这无疑是连绵的网络战火、网暴的由来之一。”
这种 “极度消极无助的社会情绪” ,在现实世界中也正加速着阶级对立和分化,为此桑德尔提出了“精英的傲慢”这个我们无法回避的现象:
“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人们对待成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那些成功人士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靠的是自己的努力,是因为他们的优绩,并且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市场给予赢家的所有好处。在这样的心理暗示下,他们开始相信那些在底层挣扎的人也一定是罪有应得。”
恰恰是这种 “精英的傲慢”刺激了民粹主义的逐步抬头 , 在美国,民粹主义反扑精英的原因之一,就是工薪阶层认为精英瞧不起他们。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在民粹主义抬头的时刻,越要警惕一种卢梭式的“普遍意志”。
张乔木提示,卢梭的认知哲学概念,即是所谓的普遍意志。 普遍意志是社会中所有成员的意志结合到一起,如果在群体性的意志下去行动,那么我是自由的,因为这个意志也是我个人的意志。当一个人的意志和普遍意志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强迫他加入到普遍意志中去。
在这种“普遍意志”下,我们必须要放弃个人意志,进入到普遍意志的思维状态里去。为了实现社会整体性的普遍意志,甚至可以用强制的手法去实现它。这种思想形成了强制性社会体制的基石。
卢梭这种思想后来的追随者都是谁? 墨索里尼、**,还有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
“普遍意志”的思想,曾让20世纪的人类遭遇了“人性的深渊之恶”,但在21世纪,这种惨剧还会继续重演吗?对此,我并不乐观,眼下的世界局势正在逐步给出答案……
为此,在采访中,钟叔河就提醒过许知远: “历史的变化不是匀速的运动,而是加速度的运动,将来你会看到很多变故,也会经历很多事情,到那个时候你会回想起今天我们的谈话。”
没错,说不定某时某刻,我们又会被迎头砸来的“历史时刻”所惊诧,然后成为一段历史的“全新开端”,如果,在未来的某一瞬间,我们真正遭遇了这种“开端”,我们该如何面对?
第二个问题:我们又将如何?
张乔木首先否定了这种“历史循环论”的思考模式,他的角度是: “一个人文主义者应该坚定地同机械主义、决定论、宿命论做最持久的斗争,因为这不仅关乎自由意志,更关乎人类的道德。决定论就是一个悖论,它会架空人类的道德。”
所以,一个人文主义者,应该相信自由意志,直面现实而非想象去迎头扑向这个真正的世界。
张乔木用他的“自由意志”,在看似受限的世俗空间中,打造了那个颇有流量的“思想史万有引力”视频号。他的建议是: “先不要去想有用无用,要把你的“知识”放到观念的自由市场中去竞争,如果市场就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我们不妨也把知识作为一个市场的产品,卖不出去,是因为你没有竞争力。曲高和寡说白了怨不得读者粗鄙,而是输出者自己的问题。”
呼吁回归现实世界,似乎是大多数思想者的主流建议,项飙提倡“关注附近”的现实行动不必多言。景凯旋也断言, 要过一种值得过的人生,那就是生活在真实中,别无他法。
罗新则建议记录现实,因为 记录现实就是一种抵抗,就是一种行动,而且是现实的行动、负责任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记录的人,就是行动的人。
劳东燕则建议,如果在现实中遭遇不公,要通过法律手段,具体的反抗: “因为每个人都乖乖地服从,治理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就永远都得不到改变。有人不服,进行反抗,你会发现其他人也会效仿,提意见的人多了,治理方式中的问题也会有所改变。我认为这才是良性的关系,从长远来看更好,而不是眼下苟且的让步。每一次苟且的让步,都会使得自身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
可,万一,我是说万一,我们还是遭遇到了“历史循环论”的诅咒,我们又该将如何面对呢?思来想去,在那种环境中,最靠谱的或许还是钟老的那两句忠告吧:
“我不是有勇气或者有可能讲我所有想讲的话,但是我绝不讲一句我不想讲的话。”
“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读的,要我们死我们是不得死的。”
这两句话仔细想其实还挺儒教价值观的,基本就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现实表达,在时局动荡的时刻,要懂得惜身,没必要死磕。
如逢无道乱世,说假话害人是绝对不可能的,让我自己把自己逼死?那更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孔子倒是反复强调过,人有时当可“杀身成仁”,但关键看那个世道值不值得你“舍生取义”……
以上就是多谈谈问题丨今天为何如此,一个是今天为何如此的详细内容,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更多请关注倾诉星球其它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