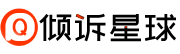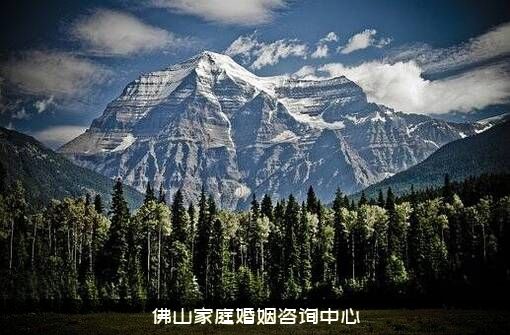关于没有比核武器更极端的事物了很多人还不了解,今天小编就为大家整理了相关内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本篇原题《可想象性》,是核主题短篇小说集《爱因斯坦的怪兽》的导言,也是一篇作者用于与人论战的文章。在作者马丁•艾米斯的心目中,“爱因斯坦的怪兽,指的是核武器,但也指的是我们。我们就...,接下来具体说说其实在核武器政策的整个历史上幼稚化就从来没有消退过
近期,万众瞩目的诺兰新片《奥本海默》上映。核武器的发明,实现了物理学意义上的进步,同时也给战后人类留下一道永恒的道德难题。
本篇原题《可想象性》,是核主题短篇小说集《爱因斯坦的怪兽》的导言,也是一篇作者用于与人论战的文章。在作者马丁•艾米斯的心目中,“爱因斯坦的怪兽,指的是核武器,但也指的是我们。我们就是爱因斯坦的怪兽,不是完全的人类,至少现在不是。”

▲ 电影《奥本海默》剧照
我出生在1949年8月25日。
四天之后,苏联人成功试爆了他们靠前颗原子弹,核威慑也就此诞生了。
就是说我只有那么四天无忧无虑的日子,这已经远胜过那些比我更年轻的人了。
我也没能真的充分利用这几天。
我一半的时间都在一个透明罩子下面。
即使事情还没有到最糟,我出生时也是一副急性休克的样子。
我母亲说我看起来像狂怒的奥逊·威尔斯。
到第四天我恢复了正常,可世界却变得更糟了。
它成了一个有核的世界。
说真的,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我困得不行还烧得厉害。
我一直在吐,还伴随着时不时无法控制的哭泣……等到我十一或十二岁的时候,电视上开始有英国南部的核打击目标地图了:靶环是伦敦周围的各郡,靶心就是伦敦。
过去我一看到这个画面就会赶紧离开房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核武器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或者是谁把它们放进来的。
我不知道要拿它们怎么办。
我不愿意去想它们。
它们让我觉得恶心。
现在,1987年,三十八年之后,我依旧不知道该拿核武器怎么办。
而且其他人也都不知道。
如果有知道怎么办的人,那我一定还没读到他写的东西。
最极端的两大选择是核战争和核裁军。
核战争是很难想象的;但核裁军也同样难以想象 (核战争自然更触手可及) 。
我们就是无法预见核裁军,对不对?某些最终废核的蓝图——我想的是,比如说安东尼·肯尼的“理论威慑”和乔纳森·谢尔的“无武器威慑”——都难以置信地优雅又诱人;可这些作者在设想的是一个不可能的*治世界,一个像他们个人的深思一样精妙、一样成熟,而且 (最重要的是) 一样协调一致的*治世界。
核战争就在7分钟之后,可能一个下午就能完结。
核裁军又有多远呢?我们在等待。
那些核武器也同样在等待。
什么是唯一能够导致动用核武器的挑衅?核武器。
什么是核武器的优先打击目标?核武器。
什么是唯一能抵御核武器的方法?核武器。
我们要如何阻止动用核武器?威胁动用核武器。
而我们无法销毁核武器的原因,还是因为核武器。
这种顽固似乎也是核武器本身的功效之一。
核武器可以用十几种不同的方式把一个人杀死十几次;而且,在死亡之前——就像某些蜘蛛,就像汽车的大灯一样——它们似乎还能让人瘫痪。
其实它们确实是非同一般的人造物。
它们的威力来自一个方程式:当1磅鈾-235裂变之后,它的1 13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个原子所“释放的质量”再乘以光速的平方——也就是说,它的爆炸力要再乘上186000英里每秒再乘以186000英里每秒。
核武器的大小,它们的威力,都没有理论上限。
它们的愤怒惊天动地。
它们明显是这个星球上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而且它们还被大量制造出来,也并不昂贵。
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们最不寻常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们是人造的。
它们扭曲了所有生命,破坏了一切自由。
不知为何,它们让我们没有任何选择。
地球上没有一个人想要它们,可它们就在这里。
▲ 苏联的靠前颗原子弹“约瑟夫一*”
我受够它们了——我受够了核武器。
其他所有人也一样。
在我和这个奇怪的主题打交道的过程中,当我读得太多或者想得太久——我会感到恶心,生理上的恶心。
从每一种可以想象的感官出发 (然后,各种感官通感之后,还可以从更多的感官角度出发) ,核武器都会让你恶心。
这是何等的毒性,何等的威力,何等的打击范围。
它们在远处而我在这里——它们是没有生命的,我是活着的——然而它们就是能让我想吐,它们就是会让我胃里恶心,它们让我觉得仿佛我的一个孩子出门很久了,太久了,而且天色正在变暗。
这可能也是种不错的练习。
因为我会做很多那种事情,因为我会呕吐很多次,如果那些武器落下来而我还活着的话。
每天早上,每周六天,我离家开车一英里去我写作的公寓。
大概有七八个小时我一个人独处。
每次我听到空气中传来突然的尖叫或者城市生活中某种别的残忍的干扰时,或者某些不受欢迎的念头入侵我的大脑的时候,我就会无法抑制地想象事情会是什么样子。
假如我也躲过了风暴般飞射的——所有的水泥、金属和玻璃瞬间变成的——碎片造成的二次伤害:假如这一切都发生了。
我将不得不 (这会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 沿着那长长的一英里返回去,穿过火焰风暴,穿过一千英里每小时的飓风留下的残骸,穿过变形的原子,穿过趴在地上的死者。
然后——上帝保佑,如果我还有力气,而且,当然,如果他们还活着——我必须找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必须杀了他们。
我要拿这样的想法怎么办?谁又能拿这样的想法怎么办?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拿核武器怎么办,也不知道要怎么和核武器共存,但我们在慢慢学习如何动笔描述它们。
修辞的得体此时就表现出了别处没有的重要性。
核武器是最崇高的主题,也是最低俗的主题。
它是羞耻的,可也是光荣的。
你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巨大的反讽:悲剧的反讽,可悲的反讽,甚至还有黑色幽默或者闹剧的反讽;还有一种反讽简直就是暴力,前所未有的暴力。
广岛上空的蘑菇云是美丽的景象,可它的颜色来自一千吨的人血……
在话语场里有好几种写作核武器话题的糟糕方式。
有些人,你最后只能得出如此结论:他就是不明白。
他们就是没法明白。
他们就是那些在公交车站瞎吹牛的人出了书而已。
这种人号称核战争不会“那么糟糕”,尤其是如果他们能躲进他们阿姨在多赛特的乡间农舍 (或者他们现在就在阿姨的农舍里了) 。
他们看不到核武器把一切都“着重加粗”了的样子。
不能明白核武器的这一点就好像不能明白人类生活的意义一样。
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困境的缘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核“选项”的一切军事——工业,在写作的瞬间就会被其所描述的武器的自然属性变得不自然,就仿佛语言本身在拒斥与这样的思维合作 (在此意义上语言比现实严苛多了,现实早已坚定地接受了核时代的虚假真实) 。
在核“冲突管理”这个勇敢积极的世界里,我们能听到人说“先行报复”;在这个世界里,小几千万人的死亡被认为“可以接受”;在这个世界里,敌对的、挑衅的、破坏平衡的核武器对准的是核武器 (“反战略力量”) ,而和平的、防守的、更注重安全的核武器 (它们就在那里消沉,可爱地噘着嘴) 对准的是城市 (“**财富”) 。
在这个世「界里,反对现在这种现实的人被称作“偏执狂”。
“欺骗性部署模式”“密集阵列组”“基线末端防御”“核足球” (也就是核按钮) ,还有诸如BAMBI、SAINTS、PALS和AWDREY (核武器侦测、辨别和当量估算装置) 这样的缩写,“绝地武士构思” (接近光速的离子束武器) ,甚至“星球大战”本身:这些说法把你带到了运动场上——或者把你带回了育婴室。
其实在核武器政策的整个历史上幼稚化就从来没有消退过。
靠前颗核弹“三位一体” (绰号“设备”) 是被吊装到一个被称为“摇篮”的装置上就位的;在倒数期间,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广播站播放的是一首摇篮曲,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科学家们在猜测“设备”将会是个“女孩” (也就是哑弹) 还是个“男孩” (也就是一个可能毁掉整个新墨西哥的装置) 。
落在广岛的核弹被称为“小男孩”。
“是个男孩!”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如此喊道,那是1952年,“麦克” (“我的孩子”) 在比基尼环礁上空起爆……这太讽刺了,因为他们才是小男孩;我们才是小男孩。
在那之后讽刺愈发加深了。
摆出灭绝人类的架势,这个终极反人类武器本质上是个反婴儿武器。
这里我说的不是那些会死于爆炸的婴儿,而是那些永远不会出生的婴儿,那些在灵魂接力赛里排队一直等到时间尽头的婴儿。
我开始涉足核武器是在1984年的夏天。
哦,我说我“开始”涉足,但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利益相关方。
人人都是核武器的利益相关方,即使那些号称或者真的相信他们从来没有花过一瞬间来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也是。
我们都是利益相关方。
有可能永远都不去想核武器吗?如果你不花心思去思考核武器的问题,如果你不花心思去考虑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那你的心思都花到哪儿去了?如果你不去想这个问题、这个过程、这种渗透,它或许是潜意识的、生理的、源自腺体的。
嘴里塞着一把上膛的枪的人或许可以吹嘘他从来没有去想过那把上好膛的枪,但他能尝到枪的味道,一直都可以。
我对核武器的兴趣是一次巧合的结果。
其中的两大因素是我眼看要当父亲了和我拖了很久之后终于读了乔纳森·谢尔经典的、催人警醒的研究《地球的命运》。
它让我醒了过来。
在那之前,我似乎一直都是晕厥的。
我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核武器的问题。
我只是一再尝到它们的味道。
现在我终于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觉得如此恶心了。
当道德水平从社会最顶层降到最低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的*导人们掌握着完成不可想象的事情的方法。
他们以我们的名义思考着不可想象的东西。
我们非常卑微地希望能不被杀死安度一生;与之相比更有信心的是,我们也希望自己不用杀死任何人就可以安度一生。
核武器把这样的选择从我们手中夺走了:我们可能会死去,而且死的时候腰上还围着屠夫的围裙。
我相信现代状况的很多畸形和变态都源自——也肯定是为其所凌驾的——这一巨大的预设。
我们的道德契约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而且还是以没有预料到的方式。
说到底,又有什么无缘无故的冲动、什么庸常的暴行,或者愚蠢的野蛮,能够比得上核战争的黑色梦魇呢?
面对让一切生命变得廉价的死亡的超级通胀,回到物理学,来回顾核的尺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夷平广岛花费的质量大约是1盎司的1/30——还不及1枚生丁重。
按照爱因斯坦的方程式,1克质量就有相当于12500吨TNT炸药爆炸的能量 (再带上点它自己的特质) 。
乔纳森·谢尔是这么写的:
……通过使用20世纪的宇宙物理能生成的能量超越了19世纪的地球或者行星物理能生成的能量,正如宇宙远超地球一样。然而正是在地球这相对微小、脆弱的生态圈里,人类却释放了新近到手的宇宙能量。
让我们暂时忽略,当代核武器库里10亿吨级的巨大存在,转而思考一下仅仅百万吨级可以做什么:它可以给美国每一个州的首府都带来广岛式的毁灭,还能剩下大约三十枚左右的核弹。
仅仅苏联的核武器库就能杀死大约二百二十亿人——或者它本可以杀死这么多人,如果地球上有这么多人给它杀的话。
但是地球上能杀的只有四十亿人。
而我们却还在讨论导弹差距的动态原因。
没有什么差距。
我们已经住在一个导弹林立的曼哈顿上了。
或者说,已经没有地方了。
我们客满了。
同时辩论还在继续。
这是什么样的辩论呢?它的语气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关注一下战略防御计划 (SDI) 引发的争议,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这就是唐纳德·**的语气:“ (战略防御计划) 不是关乎恐惧的,它是关乎希望的,而在这场斗争中,请大家原谅我盗用一句电影台词,原力与我们同在。
”不,我们不会原谅他盗用这句电影台词。
原力也没有与我们同在。
原力在反对我们。
使用如此的言论,至少是 (含义指向极度轻浮的言论) **总统开启了“一次许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努力”。
可同时,他也承认,这一计划也有“风险”。
不幸的是,风险就是终结人类历史的进程。
“上帝是不会原谅我们的,如果我们失败了。
”勃列日涅夫在入侵阿富汗之前的峰会上是这样告诉卡特的。
卡特很喜欢这个说法,他自己也使用了它,不过做了一个*治上的修改。
“历史,”他说,“是不会原谅我们的,如果我们失败的话。
”其实勃列日涅夫说得更对。
一旦“失败”了,上帝还是有可能幸存的,历史却不可能了。
三本关于SDI的书——关于末日的三本快餐读物——最近降落到我的书桌上,两本反对,一本赞成。
《如何让核武器过时》是罗伯特·贾斯特罗写的,就是那个在航天飞机失事的第二天凭那句评论“它简直就可疑”跃上了各大报章的人。
首先,贾斯特罗申明他是多么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可能的话。
这样的终局会让他有多么后悔和遗憾 (他的语气就是那种我们熟悉的心不在焉的道德装裱,仿佛这一切都是让人不耐烦的礼貌和门面问 题) ;接着他开始处理这本书的正务了,激动地讲述“终极大战”的故事。
在这出技术崇拜的太空歌剧中,我们可以瞥见总统在冷静地“命令”这个或“决定”那个,冷静地竖起他没有试验过的“和平护盾”,而此时可以屠灭整个半球的力量正在头顶的空中逼近。
实际上,如果总统还没有被苏**使馆的手提箱核弹蒸发的话,他陷入精神崩溃之中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和这场**奇幻剧的其他所有演员一样。
对贾斯特罗来说,不可想象的东西是可以想象的。
他错了,因此我得说,在这个方面他也不够有人性,就像所有主张打核战争的人一样,就像所有的“必胜派”一样。
不可想象的就不是可以想象的,不是人类可以想象的,因为它设定的结局是一个一切人类参照系统都已经消失的未来。
SDI将永远不能被测试,那些牵涉其中的人也一样。
在这样的关头他们会如何反应谁都猜不出来。
但他们将不再是人类。
某种意义上,没人还能是人类。
在防火道的那一侧并不存在这个身份。
所罗门·朱克曼认为美国盟友们对SDI的支持,虽然是不够热烈而且一脸不好意思的,在读过贾斯特罗之后不可能还继续下去。
或许同样的结论不能用在阿伦·查尔方特身他的《星球大战:自杀还是幸存?》操着实用主义的粗糙中音欢迎了SDI。
没错,这一计划会带来“很高的风险”;没错,这一计划“要求彻底重新理解核武器控制政策的基本信条”;没错,这一计划需要花费成兆亿的美金,但它是值得的。
风险奇高,彻底的**性,而且贵得难以置信,但它是值得的——因为导弹差距的存在。
苏联人很快就要这么做了,或者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或者 (他有时候似乎是在暗示) 已经完成了。
于是我们较好也这么做……有趣的是,让查尔方特男爵烦心的不是核武器的存在——他称这一事实已无法“抹去”。
让查尔方特男爵烦心的是它们的对手。
现在,这倒是一种我们可以消除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每当和平这个话题——或者“和平”——被不耐烦地引入的时候,礼貌就从他的行文里隐退了。
“和平产业马上就像预料中的一样开始抱怨了……一群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再加上几个有用的傻瓜和苏联特工 (有意识或无意识的) 组成的联盟。
”尽管他对战争“产业”这个说法感到厌烦,他却赋予了和平产业的身份。
为什么?那些和平的工业城镇在哪里?这个产业上兆亿的预算花在哪里?在书里查尔方特讨论了美国的计划:
在欧洲部署强化辐射核弹头……马上就有反对“中子弹”的骚动——被那些头脑不好用的人说成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武器,设计来杀伤人命却能保存财产。
查尔方特不满意“资本主义的武器”这个说法,我也同意。但是他对“强化辐射核弹头”有多满意?他对“强化”有多满意?
E.P.汤普森不幸也没能找到更妥帖可靠的劝说语气。
他为自己领导的运动做出了巨大牺牲;他很聪明,他很有魅力,他很能启发人;但他不可靠。
在《星球大战》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汤普森教授证明了自己是核文学高端文风最合适的推广者。
他很风趣也很大气,写作的时候带着较好的那种有节制的仇恨。
比如说,他是如此彻底地击垮了SDI的公关攻势。
从保密文件里:
可以挖掘出无数的机会来开展大量引人注意的“运动”型社会活动……天主**也会感兴趣……此类认可努力将使得白宫在面对强大的国内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批评者时显得非常有利……还处理了“欧洲战略”问题,当下这是大问题……还可以在伦理的堂皇大道上自由驰骋 (到目前为止较好的动员方式) ……
汤普森击垮了SDI;他的分析几乎毫无漏洞。但他谁都打不垮——实际上他甚至可能动摇已经相信他的人——因为他玩世不恭的语气。
他的语气是松懈的、不耐烦的,常常不确定到让人绝望;他的语气是兴奋而危言耸听;他的语气以嘲讽愚蠢为乐。
他的反美言论( “大美利坚天生就多么道德”“地球总统”“我要你们这些人高举双手走出来”) 就和查尔方特男爵相反的偏见一样过时、一样令人厌倦、一样刻板。
查尔方特不够格当人。
汤普森只是人——太普通的人。
汤姆森还会开玩笑。
他实在是太喜欢这个玩笑了,甚至开了两次:
这个马上就要登上总统大位的人已经在警告了,这个 (容易遭到袭击的时间) 窗口可能会如此洞开,甚至“苏联人打个电话就可能干掉我们了”。“你好!**先生,则是你吗?我是勃列日涅夫同志。高举你们的双手走出来,要不我就把则个杂弹扔进窗去!”
你整个人在这样的东西面前只想往后缩。你坐回去揉着自己的眼睛,想知道它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因为在关于核问题的辩论中,和其他任何问题都不一样,这样的松懈引发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人类对核武器有一致的看法;人类的机构不是这样。我们的希望在于逐渐寻求共生。我们必须找到取得一致的语言。
我和我父亲争论核武器问题。
在这场辩论里,我们都在和我们的父亲争论。
他们缔造或者维持了现状,但他们错得离谱。
他们没能看透他们在处理的东西的本质是什么——那些武器的本质——于是现在他们就困在一个新的现实之中,困在了他们巨大的错误里。
也许只有等他们都不在了才会有一点希望。
某些极端的人相信我们应该开始杀死我们的某些父辈,在他们杀死我们之前。
这让我想起了核威慑失败的精妙三段论 (这是谢尔总结的) :“他以为我将要出于自卫杀死他。
所以他就准备出于自卫杀死我。
于是我出于自卫杀死了他。
”没错,然后他又用报复核打击杀死了我,即便他已经身登鬼域。
我们继承的现实是令人感到无比耻辱的。
我们必须试着做得更好一点。
我父亲将核武器看作不可更改的既成事实。它们永远都是必要的,因为苏联人将会永远持有它们,而苏联人又永远都想要奴役西方。削减武器条约也是没用的,因为苏联人永远都会作弊。单边核裁军就等于投降。
没错,说到底,在我看来这才是以上想法真正所承诺的。
核武器,我父亲提醒我,已经靠威慑力阻止战争长达四十年了。
我提醒他说拿破仑1815年的失意之后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并不是依靠一个全球屠宰场来维持的。
而核威慑的问题就在于它无法坚持到所有时间的尽头,那大概就是从现在开始到太阳死亡为止。
它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从内部开始。
当我说美国和苏联一样是个威胁时,我父亲就把我划入不拿民主当回事、不拿自由当回事那类人中。
可那些武器本身才是真正的威胁。
非常讽刺的是,专制政权反倒更擅长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凌驾于*治之上的。
没有谁够得上当苏联人的对手——水平大幅下跌的*导人,深陷民主之中,深陷*治之中,在中期选举、跛脚鸭期和美国公众生活非正式的大部分人公投之间打六个月的短工。
而且还有钱的问题,钱。
看起来,在写作这篇文章时,苏联没钱再继续,而美国则没钱使之停下来。
索尔·贝娄曾经写过世上有某些邪恶——他举的例子是战争和金钱——有本事在被人认定是邪恶之物之后还能继续存在下去。
它们兴高采烈地作为邪恶,作为已知的邪恶,继续存在。
这是否又是核武器的一项成就,它们在一个不可救药的衰亡过程中集合了这种可延续的邪恶?所以最后世界终结的方式就和《卖赎罪券的人讲的故事》结尾一样,人类参与者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有 (虽然没人能找到它们) 用过的武器和没花出去的钱,武器和钱。
任何读过我父亲作品的人都多少知道点和他争执会是什么感觉。
当我告诉他我在写关于核武器的东西时,他声音抑扬顿挫地说:“啊,我猜你是……‘反对它们’的,对吧?”“让正经人尴尬”就是他的行事准则。
(有一次,在我一位朋友告诉他某种濒危的鲸鱼正在被大规模制成肥皂之后,他回答说:“听起来是种用完这种鲸鱼的好办法。
”其实他喜欢鲸鱼,我想,不过那不是重点。
)在核武器这个问题上我对我父亲一定比在别的任何问题上都更粗鲁,自从我青春期之后我就没有那么粗鲁地对待过他了。
我常常最后会说诸如:“好吧,我们只能等到你们这些老混蛋一个一个地死去之后了。
”
他常常最后会说诸如:“想想看。
只要关闭艺术委员会我们就可以大规模扩充我们的核武器库。
那些给诗人的奖金可以维护一艘核潜艇一整年。
花在一场《玫瑰骑士》演出上的钱就能让我们再买一颗中子弹弹头。
如果我们把伦敦的医院统统关掉,我们就可以……”某种意义上这种讽刺是很准确的,因为我只是在不停地谈论核武器;我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我们放弃了这个话题。我们的争论会友好地结束。我们最后转而欣赏起我那还是婴儿的儿子。也许他将会知道该拿核武器怎么办。我也必须去死。也许他会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那必须是非常极端的,因为再没有比核武器以及它能做到的事情更加极端的东西了。
文字 丨 选自《爱因斯坦的怪兽》,[英]马丁•艾米斯 著,肖一之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9
图片丨 选自电影《奥本海默》剧照
编辑 丨 将然
以上就是没有比核武器更极端的事物了(其实在核武器政策的整个历史上幼稚化就从来没有消退过)的详细内容,希望通过阅读小编的文章之后能够有所收获!更多请关注倾诉星球其它相关文章!